◎欢迎参与讨论,请在这里发表您的看法、交流您的观点。


现行法律法规尚未对短线交易收益的计算方法及归入程序作明确规定,人民法院在司法实践中也尚未形成一致裁判意见,董事会及董事在实务操作中面临法律难题及履职风险。本文旨在结合立法及实务现状,就该问题进行探讨并提供合规建议。
作者丨黄博曦 江学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第四十四条[1]规定了短线交易归入制度,即上市公司(含新三板挂牌公司,下同)持有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下简称大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下简称董监高)等特定投资者在6个月内,将本公司股票或者其他具有股权性质的证券买入后又卖出,或者卖出后又买入,由此所得收益归该公司所有,公司董事会应当收回其所得收益。然而,自1993年《股票发行与交易管理暂行条例》引入短线交易归入制度以来,在1999年《证券法》立法及历经多次修订/修正后,我国在法律法规层面仍未明确规定短线交易收益的计算方法。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证监会)于2023年7月21日公布的《关于完善特定短线交易监管的若干规定(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征求意见稿》)也未填补这一漏洞,仅规定交由证券交易所或全国股转公司具体规定。[2]短线交易收益为买卖证券的差价,在复杂的交易中,买入卖出价格各不相同,将不同买卖进行不同匹配的计算方法所得的收益结果会有所不同,规则层面的不明确造成了实务中上市公司、司法机关对短线交易收益计算莫衷一是,方法不一。
短线交易归入制度作为吓阻大股东和董监高等特定投资者内幕交易行为的事前手段,对保护中小投资者利益意义重大。[3]在上市公司治理层面,准确计算、及时归入短线交易收益也是董事会及董事勤勉尽责的要求,在近年来A股上市公司短线交易频发[4]以及《证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逐渐强化董事履职责任的背景下,董事会合法合理行使短线交易收益归入权的重要性也逐渐凸显。本文将综合《证券法》《公司法》等有关规定及实务现状,对短线交易收益的计算方法以及董事会行使归入权的程序进行探讨、给出合规建议,以期对参与短线交易收益计算及归入的实务人士有所启发。
一、实务中常见的短线交易收益计算方法
根据笔者经公开渠道检索的情况,证监会/证券交易所关于短线交易的行政处罚/监督管理措施/自律管理措施决定中一般不会涉及短线交易收益的计算,上市公司通过诉讼追讨短线交易收益的案件极少(原因可能在于:第一,实施短线交易的行为人为上市公司的大股东、董监高等特殊投资者,偿还能力较强,且及时将所得收益归入上市公司有助于行为人减轻或免除因短线交易导致的行政处罚或监督管理措施,上市公司不需通过诉讼的方式追讨其所得收益;第二,有关规定对短线交易认定要件的规定较为客观、具体,行为人买入、卖出证券的行为均有留痕,上市公司及行为人之间不需通过诉讼解决事实争议等。),实务中主要涉及短线交易收益的计算方法的情形为上市公司在相关公告中披露。实务中各上市公司及法院采取的常见的短线交易收益计算方法如下:
(一)最高卖价减最低买价法
该计算方法具体为:将法定期间内卖价与买价相匹配,最高卖价匹配最低买价,次高卖价匹配次高买价,直至全部匹配完成,依匹配顺序计算差价,只计收益不计亏损。计算公式可表示为:(最高卖价-最低买价)×证券数+(次最高卖价-次最低买价)×证券数,……依此类推。
经笔者检索,尚未有法院在公开的裁判文书中采用该计算方法,但该计算方法在上市公司内部处理短线交易事件时较为常见[5]。笔者认为采用该计算方法可能存在以下优势:第一,在涉及复杂的短线交易时,可以避免对每一笔买卖进行识别和对应,一定程度上简化了核算成本;第二,确保收益全面追缴,使可收回的收益最大化;第三,强化对相关人员的警示,并向公众彰显对公司及其投资者利益的保护。美国和我国台湾地区均采用最高卖价减最低买价法,但也有观点认为该计算方法最为苛刻,具有惩罚性,可能导致行为人在整体亏损的情况下仍上缴收益[6]。
(二)先进先出法
该计算方法与会计上的先进先出法的含义和操作相同,即在法定期间内按照买入股票的时间先后顺序逐一对应每个交易日的卖出来计算收益。[7]在某短线交易案中,审理法院便采取了先进先出法并说理如下:“因在认定短线交易时系以股东持股达到5%后六个月内的买进卖出的反向交易确定,存在时间先后的对应关系,故在计算收益时亦应按买进、卖出的先后顺序确定更具有合理性,即通常所说的先进先出,即以持股达到5%以后所买入的股票的时间先后顺序逐一对应每个交易日的卖出来计算收益”。[8]
(三)平均成本法
平均成本法本质上是以卖出股票所得总金额,减去买入股票成本总金额,得出收益数额。计算公式可以表达为:(卖出平均价-买入平均价)×短线交易证券数。
平均成本法在操作上比其他方法更为简便,也属于近年来上市公司在实务中较为常用的计算方法[9],在为数极少的司法实践中亦有法院采取了该方法,例如京泉华案[10]。但正如美国联邦第二巡回法院在首次确立最高卖价减最低买价法的Smolowe v. Delendo Corp.案中的评价,平均成本法有其弊端:内部人则能够以交易损失抵扣交易盈余,若盈亏互抵而导致无盈余时,无异于“鼓励”内部人在先前交易中尚有亏损的情形下,进行更多短线交易以弥补损失,使内部人交易更趋频繁。[11]
二、董事会行使短线交易收益归入权的合规建议
《证券法》第四十四条规定,公司董事会应当收回行为人短线交易所得收益。《征求意见稿》第十三条规定:“特定身份投资者涉及特定短线交易行为的,所得收益归该公司所有,特定身份投资者未主动归还公司的,公司董事会应当按照《证券法》等规定收回其所得收益。”但对于董事会具体如何决策、如何行使归入权,《证券法》及《征求意见稿》均未作规定。
根据《公司法》第一百八十八条、第一百八十九条的规定,董事执行职务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公司章程的规定,给公司造成损失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连续180日以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1%以上股份的股东有权提起代位诉讼追究涉事董事的责任。根据《证券法》第九十四条第三款的规定,董事执行公司职务给公司造成损失的,投资者保护机构持有该公司股份的,可以为公司的利益以自己的名义向法院起诉,持股比例持股期限不受《公司法》规定的限制。
如前所述,相关法律法规对短线交易收益的计算方法及归入程序未作具体规定,法院未形成一致裁判意见,以及各上市公司也未形成统一惯例。如董事会未选择正确的计算方法、未及时行使归入权或决策程序违反法律法规或公司章程,造成公司损失的,董事将面临被公司或股东要求承担赔偿责任的风险。为规避该等风险,本文建议公司、董事会及董事可考虑采取如下合规措施:
(一)原则上优先按照最高卖价减最低买价法计算短线交易收益
基于以下理由,本文建议董事会优先按照最高卖价减最低买价法计算短线交易收益:
1. 符合加重短线交易行为人法律责任的立法趋势。对于短线交易行为人的法律责任,2019年修订前的《证券法》仅规定对行为人“给予警告,可以并处三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的罚款”,现行《证券法》第一百八十九条则规定对行为人“给予警告,并处以十万元以上一百万元以下的罚款”,加重了短线交易行为人法律责任,在立法层面彰显了短线交易行为的违法性和可惩罚性。董事会按照最高卖价减最低买价法计算短线交易收益,可最大程度将行为人所得收益归入公司,对行为人进行惩戒。
2. 有利于吓阻大股东及董监高等特定投资者实施短线交易行为,维护中小投资者利益。限制短线交易的实质在于防范内幕交易和操纵市场,防止内部人利用信息优势牟利。董事会按照最高卖价减最低买价法计算短线交易收益,可最大程度将行为人所得收益归入公司,对大股东及董监高等特定投资者起到最大程度的吓阻作用,从而维护信息处于劣势的中小投资者的利益。
3. 有利于控制董事的履职风险。如前所述,根据《公司法》《证券法》的相关规定,如董事会未选择正确的短线交易收益计算方法,造成公司损失的,董事将面临被公司或股东要求承担赔偿责任的风险。董事会按照最高卖价减最低买价法计算短线交易收益,可最大程度将行为人所得收益归入公司,规避公司或股东要求承担赔偿责任的风险。
但是在部分例外情形下,董事会也可以按照先进先出法或平均成本法计算短线交易收益,例如在各组买卖交易完全互相匹配的情形下,此时按照先进先出法或平均成本法计算收益显然更贴近交易的实际情况。
另外当短线交易行为人“越过”董事会主动向公司支付所得收益时,董事会也应当根据上述建议合理选择计算方法,对行为人主动支付的收益金额进行复核。如行为人计算的短线交易收益金额小于董事会计算的金额,董事会应及时通知行为人并将收益差额补充归入公司。
(二)董事会对短线交易收益计算及归入相关事项进行决策时关联董事应当回避表决
《公司法》第一百三十九条对关联董事回避表决作了原则性规定,即上市公司董事与董事会会议决议事项涉及的企业或者个人有关联关系的,该董事应当及时向董事会书面报告,且有关联关系的董事不得对该项决议行使表决权,也不得代理其他董事行使表决权。《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二至第一百八十五条规定了关联董事应回避参与涉及董事违反忠实义务事项的表决,具体包括:(1)董事、其近亲属、本人或其近亲属控制的企业以及其他关联人与公司订立合同或进行交易;(2)利用职务便利为自己或他人谋取属于公司的商业机会;(3)未经公司内部程序自营或为他人经营与本公司同类业务。
基于上述规定,表决权回避制度的立法目的是避免将董事利益置于与公司利益相冲突的境地。[12]当董事实施短线交易后,董事会依法应当将其所得收益归入公司,在这一事项的决策中,涉事董事的利益(保留所得收益)和公司利益(归入所得收益)便存在冲突。如前所述,不同的计算方法会导致短线交易收益金额的不同,甚至可能差异巨大。从趋利避害的人性角度出发,如涉事董事不回避表决,难以规避涉事董事在参与表决中支持有利于自身的计算方法并影响其他参会董事,从而规避部分收益的归还。因此,在上市公司董事实施短线交易的情形中,董事会对短线交易收益计算及归入相关事项进行决策时,关联董事应当回避表决。
(三)将利息、股息红利纳入应当归入的收益范围
短线交易发生后,除了可能产生证券买卖差价的所得收益外,在行为发生至所得收益归还公司的时间内,会产生利息,还可能产生股息红利,本文认为这些利息和股息红利也应当纳入归入公司的收益范围,理由如下:
1. 利息属于法定孳息,是短线交易所得收益在归还公司前产生的,根据民法理论,法定孳息归原物所有人享有,利息作为所得收益的法定孳息,所有权也应属于公司。因此应从短线交易发生次日起,比照银行同期存款利率,将利息归还公司。以往案例中亦有审理法院支持了此观点。
2. 如短线交易为先买入后卖出的形式,行为人可能在买入证券后,获得公司分配的股息红利。有观点认为,股息不是利用内幕消息之所得,应当将其排除在应当归入的收益之外,但短线交易归入制度采取的是严格责任,将股息红利纳入归入范围,可以更为广泛地防范短线交易以及内幕交易的发生,因此本文建议将股息红利纳入应当归入的收益范围。
但是,短线交易的收益不应包括行为人进行短线交易所支付的手续费、税费、佣金等费用,如果也纳入应当归入的范围,则相当于行为人支付了双倍的费用。
结语
短线交易归入制度是我国吓阻大股东和董监高等特定投资者内幕交易行为、保护中小投资者利益的重要事前手段,在上市公司治理层面,准确计算、及时归入短线交易收益也是董事会及董事勤勉尽责的要求。但因为相关法律法规未对短线交易收益的计算方法以及董事会行使归入权的程序作明确规定,且司法机关未形成一致裁判意见,导致实务中存在难题,董事面临履职风险。本文综合《证券法》《公司法》等有关规定及实务现状,就短线交易收益的计算方法以及董事会行使归入权的程序,给出原则上优先按照最高卖价减最低买价法计算短线交易收益、董事会对短线交易收益计算及归入相关事项进行决策时关联董事应当回避表决以及将利息、股息红利纳入应当归入的收益范围等合规建议。
[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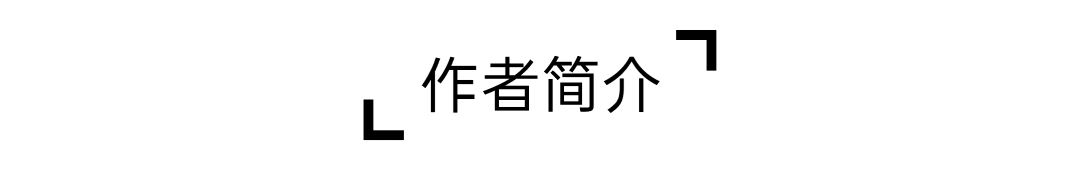

黄博曦 律师
深圳办公室 资本市场部

江学勇 律师
深圳办公室 合伙人

业务领域:中国内地资本市场,投资并购和公司治理,合规和调查
行业领域:城市基础设施,能源和电力

《董事民事责任的强化与限制(三)——公司限制董事责任的可能路径》
《董事民事责任的强化与限制(二)——董事履责、担责的现实困境和限制董事责任的必要性》
《董事民事责任的强化与限制(一)——董事责任的强化》
特别声明
以上所刊登的文章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不代表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或其律师出具的任何形式之法律意见或建议。
如需转载或引用该等文章的任何内容,请私信沟通授权事宜,并于转载时在文章开头处注明来源于公众号“中伦视界”及作者姓名。未经本所书面授权,不得转载或使用该等文章中的任何内容,含图片、影像等视听资料。如您有意就相关议题进一步交流或探讨,欢迎与本所联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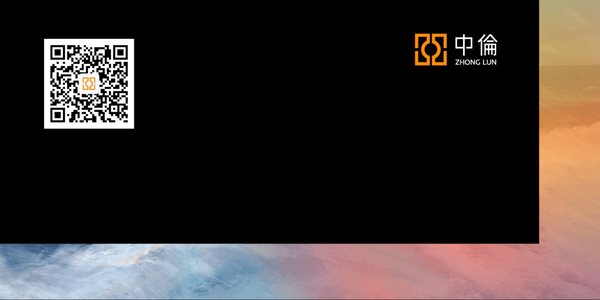

◎欢迎参与讨论,请在这里发表您的看法、交流您的观点。

工作时间:8:00-18:00
电子邮件
扫码二维码
获取最新动态
